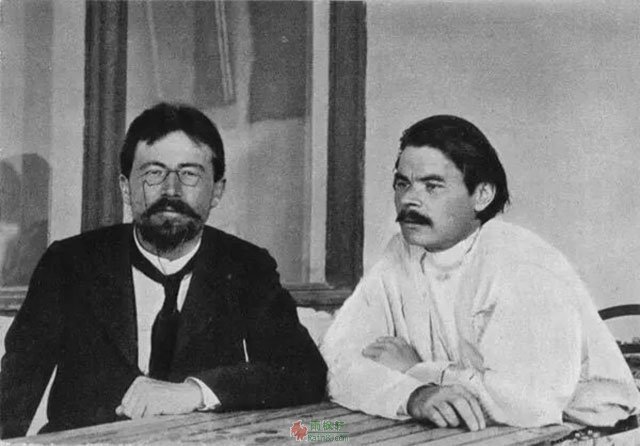
高英培、范振钰有段相声,叫《破镜重圆》,讲一对夫妇的分与合。两人结婚二十多年,和睦恩爱,下面有子有女,谁见了都羡慕。然后,有一天早起,两人在衣柜的大镜子前穿衣,妻子比丈夫矮一头,丈夫随口就说:“嘿,你只到我肩膀。”妻子立刻顶了一句:“嫌我矮?你找个儿高的去呀!”
互相冲撞了几句,俩人就此不说话,直到闹到分居。后边如何和好的事且不提了,过去的相声也许不很有笑点,但作者和演员常常有一颗爱人之心。你有了点经历,你就明白《破镜重圆》写得多么真实,需要何其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感觉,多少亲密关系死于“一言不合”,多少自以为知根知底的人,突然发现原来两人之间的隔阂那么深。
隔阂,也是契诃夫小说里最稳定的主题。但这是一个深刻的心理现象,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体会。对二十来岁的人而言,世界尚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,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冒险,每一天都可能出现新的人、新的奇遇,碰了钉子没关系,换一个方向掘进即可,总能指望有人听进去自己的声音。
然而,一旦你的生活格局稳定下来,隔阂的困扰就出现了:当你有了朝夕共处的人,如果他或她突然变得完全不能理解你,你肯定要痛苦死的。
这种痛苦是最无力纾解的。生活对你最大的考验不是给你安排了多少个敌人(哪怕你把在朋友圈里所有晒优越的人都视为你的敌人),而是让你发现,自己没法跟正常的人、跟朋友、跟亲人沟通。越是年深日久的友谊亲情,越是脆弱——这一点,在契诃夫之前,没有谁真正把握住,并写成耐嚼的故事过。
他的小说独一无二,偏离了俄国传统,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距离遥远,要说其中富有诗意,但又同俄国诗圣普希金有很大一段距离。普希金写过的经典故事《黑桃皇后》,或想一想莫泊桑最有名、争议也最大的《项链》,还有欧·亨利之类,他们的故事都建立在一种谋划之上,效果是谋划出来的:鬼神掺合,机缘巧合,人物突然发疯,项链突然被宣布为假的,诸如此类。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,人物押下了一大笔赌注,结果事与愿违,输个精光——作家就以此取悦读者和观众。
在契诃夫小说全集重装发布的时候,我若有所思地想到,这不是个适合契诃夫生存的舆论环境,因为,这个环境已经完全刷上了媒体的颜色。媒体希望制造给公众的饲料,最好拥有《项链》那样的结尾;媒体让人整天关心的就是所谓“神转折”,培养了一批紧盯悬念、期待转折的看客,一堆“分析人士”在新闻事件里寻找逆转的可能,津津乐道地分析。如果没有转折,那么交锋也是必需的:必须有两方人士围绕一件事情“辩论”,这样,静态的事才能动起来,发生在特定人身上的事情,才会显得和其他人相关。
契诃夫写的却是内心戏,例如隔阂。隔阂这种东西,从外在是看不出来。新闻里说一对金童玉女分手,你能看到他们的隔阂么?不,你看到的只是“般配”这种肤浅的东西,你意淫着那个男人/女人,出身好,情商智商超高,我喜欢,让给我吧……对不住了,契诃夫不来调动或满足你的这种幻想。比如说,一篇《睡眠》,说一个孤儿照料一个婴孩,婴孩晚上哇哇大哭,吵得她睡不好觉,她就把孩子给闷死了——也很像一条社会新闻,可是他让读者看到,在残酷和愚蠢行为的背后,是孤儿怎样的人生经历。比如《安纽达》,主角是一个无家可归,靠着给公寓里的大学生做情妇度日的女孩,她脱掉上衣,给她的第n任男友,一个准备解剖课考试的医学院学生做活体标本。她心里明白,男孩一毕业,他们的关系就会了结,他会进入一段体面的婚姻,而她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能收容她的人——不敢奢求爱。
在表面平静如水的现实过程下捕捉住内心的“一动”,这是契诃夫厉害的地方。他不是莫泊桑能比肩的。你过去若对契诃夫有个印象,顶多只觉得他是个揭露社会冷漠的行家,可你在体会过那种无法归咎于谁的孤独之痛之后,才慢慢明白,人的内心戏,远比外在的聚散离合、嬉笑怒骂复杂得多。
在《复活节之夜》里,主角坐一条摆渡船去听弥撒,船夫是个修士,一路上一直在念叨一位刚刚早逝的同事,说他给教堂写的赞美诗有多好,说他多少次听到泣下。从教堂回来,主角发现,那个修士还在撑船,他心里一动:这个复活节之夜,为什么还没有人来替代他?为什么不派一个不太敏感的人来替代他,而让他毫无牵绊、无拘无束地沉浸在知音的幸福之中呢?
如果你一直不去体察别人的内心活动,你就会觉得别人没有内心活动,就不会感觉到别人有细微的情感需求。迟钝的大众,从来是以类别代替具体的人的,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东西笼统地视为“不正常”,把悲剧的发生看作人之恶在作祟。但契诃夫对简单的恶不感兴趣——他总是在冷漠与残酷之间划出界线:冷漠意味着同情的丧失,或者,一个人出于种种原因没能表达他的同情。在契诃夫的小说里,最坏的并不是作恶多端,而是两个人没能“交换”他们的感情,两个人,各自都断定对方自私,从而愈行愈远。
契诃夫不是要人们遗忘恶,也不是要人们在恶中看到善——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鼓吹“要爱你的敌人”。他是个农奴的孙子,一位暴戾父亲的儿子,而且早在二十多岁时,就知道肺结核病不会让他活很久。可他从来不信上帝,也不信转世投胎福祸报应之说。他是世俗的,属苍生的。之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失落,一些喜悦,一些嫉妒、悲伤、痛苦、疯狂需要回应,是因为若非如此,每个人都将只有孤星一样的命运。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和其他人类的关系之中。如果世界是个地狱,那是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地狱;如果我们想要快乐,就必须和身边的人在一起。
契诃夫小说的“点”,神经稍微粗放一点,就get不到,或者问出一个“so what?”的问题。他的小说挑战读者,也培育读者,磨他们的心。你想想,在契诃夫所处的19世纪末,没有互联网,没有购物商场,没有空调,没有足球联赛、电影、电视,在那之前的几百几千年,以今天的标准来看都是“无声”的,人们根本没有即时表达自己的机会。你再想想俄罗斯,冬夜苦寒,除了围坐在火堆边上互相说故事外,人们别无娱乐方式;那些故事当然大多数是离奇惊悚,怪力乱神,突然之间,有一个叫契诃夫的人,用大众都能懂的语言,叙述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,别有匠心地露出了其中被人忽略的动人之处,他在26岁上就已发表了将近四百篇前人从未写过的故事……这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现象?
